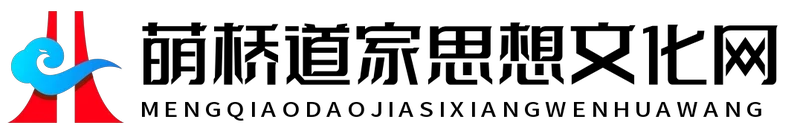内容摘要:隋吴通墓志,近出河南洛阳。墓志盖刻有八卦符号及劝诫后世掘墓者镇墓文字若干,墓志正文四周刻有后天八卦及筮数互体卦画符号,配以隶书甲乙、丙丁、庚辛、壬癸等干支,志文格式及部分文辞内容来自陶弘景《真诰》,为他志所罕见,对于探讨隋初道教发展状况具有重要史料价值。关于吴通墓志所反映出的道教文化内涵,推测其形成缘由有二:一,道教参与丧葬活动由来已久,墓志与镇墓文结合有其历史渊源;二,隋初道教兴盛,茅山宗的上清法经北传,并逐渐成为北方道教主流,加之吴通本人信奉道教,故其墓志刊刻取法道教经典。
关键词:墓志;镇木文;真诰;道教
作者简介:王连龙,1975年生,历史学博士,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隋唐时期包含道教文化因素的墓志,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道士墓志,另一类为信仰道教的民众墓志。对于道教文化研究而言,后者更具有史料价值,因为它能更为直接地反映出民间信仰的真实状态。但略为遗憾的是,目前学术界关于带有道教文字及符号的民众墓志与“敕告文”等镇墓文石刻的区别多认识模糊,[1]从而影响了对其所反映道教文化内涵的深入研究。本文所欲探讨的吴通墓志,作为道教民众墓志与“敕告文”等镇墓文石刻之结合体,有着极为重要的研究价值。
吴通墓志,全称《大隋洺州广年县令故吴明府墓志铭》,近出河南洛阳。志石一合,志盖阳文刻篆书“大隋故吴明府墓志铭”9字,3行,行3字。志盖三行篆文之间又有隶书小字两行,内容为六月、九月两次筮占,及劝诫后世掘墓者的镇墓文字若干,他志殊罕见。志石高广57厘米,凡14行,满行15字,共计208字。志文记载了隋初洺州广年县令吴通的家族世系及宦绩功业,尤以墓志所反映出的道教文化内涵,不乏有益于学术者。今拟证之以传世文献及碑志材料,对该墓志略作考证,以期于隋初道教文化研究有所助益。
为行文之便,先誊录志盖及志文如下:
志盖:
大隋故吳明府墓誌銘
萃,六月卦,大吉之。謙,[2]九月卦。塟後壹遷捌/百年,吳奴子所發掘。誡吳奴子厚塟之,得大吉昌。
志文:
大隋洺州广年县令故吳明府墓志铭
天帝告地下塚申王氣、五方諸神、趙子/都等:大隋開皇廿年歲次庚申十月丁/巳朔廿九日乙酉,君諱通,字僧伽,勃海/安陵人也。祖宜,趙州司馬。父齋,幽州長/史。君齊徐州散騎,開皇三年,勅使郃陽/公梁子恭版授洺州廣年縣令,至十七/年九月遘疾,春秋八十有八,終於家第,/與夫人謝氏葬於洛城西南十里營墳。/恐谷徙山移,乃為刊記:生值清真/之氣,死歸玄宮。翳身冥鄉,潛寧澄虚,辟/斥諸禁諸忌,不得妄為害氣,當今於後/見世子孫昌熾,文詠九功,武備七德,生/生富貴,興王無窮,壹如土下九天律令。
志主吴通,及祖吴宜、父吴斋,不见传世典籍所载,可补史阙。志谓吴通勃海安陵人(今河北吴桥县北),曾官齐徐州散骑常侍,开皇三年(583),敕使郃阳公梁子恭版授洺州广年(今河北永年县东)县令。散骑常侍,魏文帝黄初年间合散骑与常侍二官而置,侍奉禁内,掌劝谏之事。历代沿设,北齐属集书省,仍习旧职,掌讽议献纳,兼以出入王命,职位不显。梁子恭,史有所载。《隋书》卷七十三《赵轨传》云:“(赵轨)有能名,……在州四年,考绩连最。持节使者邵阳公梁子恭状上,高祖嘉之,赐物三百段,米三百石,征轨入朝。”《旧唐书》载同,并记其事在开皇中。时持节使者梁子恭巡行州县,察长吏贤不肖,礼高年,赈穷乏,故有张轨入朝及吴通版授县令之事。版授,即版授高年,系盛行于北朝时期的一种旨在善待耆老的职官除授制度,规定有德望之老者在一定年龄授予相应虚衔官职。如北周武帝保定元年(561)正月,“甲戌,诏先经兵戎官年六十已上,及民七十已上,节级板授官”。[3] 隋承前制,杨广大业元年(605)诏书:“高年之老,加其版授,并依别条,赐以粟帛。”[4] 大业七年(611)又诏:“其河北诸郡及山西、山东年九十已上者,版授太守;八十者,授县令。”[5] 按,开皇三年吴通版授县令,时年七十四岁,年龄及除授职官大体符合北周版授之制,反映了隋初版授制度的真实状态。墓志最后云吴通开皇十七年(597),享年八十八岁,卒于家。逆推之,吴通当生于北魏永平三年(510),历北魏、东魏、北齐及隋四朝,可谓颐年有道。
与志文所载史实相比,墓志形制及文辞内容所反映出的道教文化内涵更为值得关注。
首先,吴通墓志在形制上所蕴含的宗教意识与道教有关。
与其他隋志有别,吴通墓志盖三行篆文之间又有隶书小字两行,内容为六月、九月两次筮占,及劝诫后世掘墓者的镇墓文字若干。稽之已见墓志材料,在志盖处书写劝诫文字的现象于北朝时期已经出现,如北魏济阴王元郁墓志盖即有“仰为亡妣用紫金一斤七两造花冠双钗,并扶颐,若后人得者,为亡父母减半造像,今古共福,安不慕同”[6] 等文字。但如吴通墓志这般以筮卦推演来震慑掘墓者的现象,可谓鲜见。
而且与墓志盖相对应,吴通墓志正文四周刻有后天八卦及筮数互体卦画符号若干,间配以隶书甲乙、丙丁、庚辛、壬癸等干支,与式盘、铜镜等器物上的同类符号相对应,无不反映出极为浓厚的道教文化因素。相类图案,目前仅见于隋开皇二十年(600)马稚墓志盖。[7] 二志刊刻时地一致,道教风格相类,志文又同为隶书,推测二志书丹及刊刻当出于一人之手。
此外,吴通墓志文的第一行“大隋洺州廣年縣令故吳明府墓誌銘”用篆隶杂糅书体书写,与志文整齐划一的隶书明显有别。按,这种志文中篆隶真书杂糅的现象习见于北朝墓志,如北魏孝昌二年(526)《寇治墓志》、《寇偘墓志》等。已有学者指出这种现象的出现与道教信仰有关。[8] 应该说,这种观点是可以成立的。据《魏书》卷一百一十四《释老志》所载,道士寇谦之自称受天师之位,太上老君玄孙李普文授其《录图真经》,“古文鸟迹,篆隶杂体,辞义约辩,婉而成章”,遂创篆隶杂糅书体。又《云笈七籤》卷七《三洞经教部·八显》云:“八显者,一曰天书,八会是也;二曰神书,云篆是也。三曰地书,龙凤之象也。四曰内书,龟龙鱼鸟所吐者也。五曰外书,鳞甲毛羽所载也。六曰鬼书,杂体微昧,非人所解者也。七曰中夏书,草艺云篆是也。八曰戎夷书,类于昆虫者也。”亦可佐证吴通墓志这种篆隶杂糅书体与道教文化有关。
其次,吴通墓志文格式及部分文辞内容直接来源于道教经典。
相比马稚墓志,吴通墓志所反映出的道教文化气息更为浓厚。这一点除了表现在卦画及篆隶杂糅书体之外,还集中地体现在志文格式及文辞内容上。就志文格式而言,上举马稚墓志文左侧有“天帝告塚中王氣、五方諸神、趙子都等馬先生善人”20字,与志文突显不类,不相协调,志文序铭却与其他墓志格式相同,并无二致。吴通墓志虽亦见“天帝告地下塚中王氣、五方諸神、趙子都等”句,然该句列入墓志铭下,与志文有机地融为一体。更为明显者,吴通墓志铭文部分并非如传统墓志文对死者的颂扬及悼念之辞,而是“一如土下九天律令”等道家用语。稽之隋唐出土碑志,行文与吴通墓志最为相似者应为唐早期赵洪达镇墓文:[9]
天帝告土下冢中王氣、四方諸神、赵公明等:唐國許州扶溝縣□川公趙洪達,年四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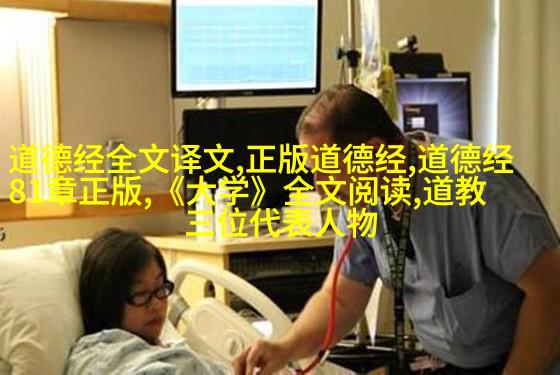
目前学界已经证明,这段镇墓文内容及格式来自于陶弘景《真诰》。[10] 为方便比较,此处把《真诰》卷十相关文字誊录出:
夫欲建吉冢之法,……题其文曰:“天帝告土下冢中王气、五方诸神、赵公明等:某国公侯甲乙,年如千岁,生值清真之气,死归神宫,翳身冥乡,潜宁冲虚,辟斥诸禁忌,不得妄为害气,当今子孙昌炽,文咏九功,武备七德,世世贵王,与天地无穷,一如土下九天律令。”
细审吴通墓志行文,亦不难发现其与《真诰》文多有契合,特别是首句及铭文部分,均以《真诰》文为本。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吴通墓志有名讳、籍贯、世系、宦绩及葬地等内容,与《真诰》文略异。究其原因所在,当为这些内容本属墓志铭所有,吴通志文前有“墓志铭”之语,即是明证。但必须承认,吴通墓志在行文格式及文辞内容上采用道教镇墓文,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墓志。换言之,如果在性质上加以详细划分,吴通墓志定位于墓志铭与镇墓文之结合体,更为合适。也就是说,在墓志文及镇墓文兼及角度上,吴通墓志与马稚墓志及赵洪达镇墓文均有所区别,从而形成隋唐墓志发展史上的一个特例。
关于吴通墓志缘何具有如此丰富的道教文化内涵,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本文推测其形成缘由大致有二:
其一,道教参与丧葬活动由来已久。道教自东汉形成以来,以其宣扬宗教仪式具有赐福、赫罪、解厄等功能,从而与丧葬活动密切关联。东汉始见出现的大量具有道教文化因素的镇墓文及买地券,即是这种密切关系最直接的证明。特别是这一时期,南北朝间那种成熟的墓志文体尚未形成之前,这些镇墓文及买地券相应地表现出了部分墓志的功用。如东汉永元四年(92年)绥德招魂辞,上节文辞记载了墓主名讳、职官、卒日、葬地等本属于墓志铭的内容,下节文辞则是针对死者的那种巫文化色彩极浓的招魂文字。[11] 还有东汉建和元年(147)长安县三里村镇墓文,行文中出现了墓主卒日及享年等情况的记载。[12] 相类情况还见于东汉建宁三年(170)许阿瞿画像题记。[13] 到了魏晋时期,虽然比较正式的墓志已经出现,但在同时期的镇墓文及买地券中,墓主卒日、年龄等信息与道教用语并见的情况还是普遍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吴通墓志这种墓志铭与镇墓文相结合的形式,有着特殊的历史渊源。
其二,隋初道教兴盛背景下的墓志刊刻风气。有隋之初,杨坚虽崇信佛教,但于道教亦不无重视。开国之初,杨坚即以“以(张)宾为华州刺史,(焦)子顺为开府,(董)子华为上仪同”,[14] 对道士大加任用。开皇三年,又“于都下畿内造观三十六所,名曰玄坛,度道士二千人”。[15] 此外,杨坚还曾下令禁止破坏道教神像,为道教的兴盛发展提供法律上的保障。就宏观角度言之,隋代短暂的南北统一也为道教不同派别的融合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其时,陶弘景创建的茅山宗的上清法经开始北传,并与楼观道相结合,逐渐成为北方道教主流。更为重要的是,根据墓志所载,吴通本人即信奉道教。如吴通墓志盖刻有六月、九月两次筮占,并有卦辞若干。以吴通卒月观之,此两卦应为吴通生前所演算。吴通高龄八十有八,又精通于术艺之法,可确知其为道教信徒。据《北齐书》卷四十九《方伎传》所载,渤海有吴遵世者,少学《易》,入恒山从隐居道士游处,受开心符于仙翁,遂明占候,以易筮知名,深得北魏孝武帝崇信。吴遵世、吴通皆为渤海吴氏,生活年代相近,俱精于道术,明易筮之学,亦可为证。此外,志文还记载吴通字僧伽。按,“僧伽”,本佛教用语,省称为僧。此虽不足以证明吴通果为佛家,但其与佛教有关还是可以肯定的。与其相类,马稚墓志亦谓“入伽兰之室”云云,显然证明马稚曾笃信佛教。此外,1980年洛阳附近出土的一件隋大业元年(605)道教石雕老君造像,其铭文字里行间亦多包含佛教意味。[16]应该说,这种情况的出现与隋初佛道并重及上清派茅山宗创始人陶弘景佛道双修,以佛道互融,兼收并取的信仰原则不无关系。如此,在上清法经北传背景下,吴通崇信道教,其墓志刊刻取法道教文化因素,自然在情理之中。
综上所述,本文对新见隋吴通墓志进行了考证,并在此基础上,对该志所反映出的道教文化内涵进行了分析和溯源。目前,反映隋初道教传播与发展状况的实物相对少见,相关研究多依赖于传世文献的记载。像吴通墓志这样有文字内容,且与道教密切相关的石刻文物,可谓弥足珍贵。加之早年发现的马稚墓志,洛阳地区出土的带有道教文化因素的隋代墓志已见两方,直接反映了隋初洛阳地区民间信仰的原貌及道教文化因素对丧葬风气的影响,学术意义重大。
注释:
[1] 张勋燎、白彬:《中国道教考古》,线装书局2006年版,第1462页。
[2]为小过,非为谦,疑刊刻之误。
[3](唐)令狐德棻等:《周书》卷五《武帝纪上》,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64页。
[4](唐)魏征等:《隋书》卷三《炀帝纪上》,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63页。
[5](唐)魏征等:《隋书》卷三《炀帝纪上》,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76页。
[6]王连龙:《新见北魏〈济阴王元郁墓志〉考释》,《古代文明》20t0年第4期。
[7]马稚墓志现藏西安碑林博物馆,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有著录。相关研究有:田中华:《隋〈马稚墓志铭〉释读》,《碑林集刊》1995年第3辑,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5年版,第43—46页;陈忠凯:《隋〈马稚墓志铭〉册的“告地策”》,《文博》1989年第4期。
[8] 华人德:《论北朝碑刻中的篆隶真书杂糅现象——〈中国书法全集·三国两晋南北朝墓志卷〉编纂札记》,《中国书法》1997年第1期。
[9]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扶沟县唐赵洪达墓》,《考古》1965年8期。
[10]黄景春:《早期买地券、镇墓文整理与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4年度博士论文,第14页。
[11]榆林地区文管会、绥德县博物馆:《陕西绥德县四十里铺画像石墓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2002年第3期。
[12]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长安县三里村东汉墓葬发掘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7期。
[13] 南阳市博物馆:《南阳发现东汉许阿瞿墓志画像石》,《文物》1974年第8期。关于这段画像石题记的性质,学界有所争论,焦点在于其是墓志还是镇墓文。笔者认为,许阿瞿画像石题记部分涉及后世墓志所见内容,但是其文字同时也具有宗教文化色彩,与当时所见镇墓文相类。这种情况说明,墓志在其早期发展阶段,依附于镇墓文、买地券等宗教器而存在,并未形成独立状态。
[14](唐)魏征等:《隋书》卷七十八《艺术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774页。
[15](唐)杜光庭:《历代崇道记》,《道藏》,第18册,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14202页。
[16] 谢新建:《洛阳东马沟出土隋代石雕老君像》,《中原文物》1984年第3期。